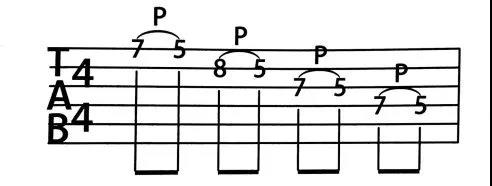那个叫巴赫的人,他不是上帝
伯恩斯坦说:“巴赫是一个人,而不是上帝,但他是上帝的人,他的音乐自始自终都受到了上帝的恩泽。”
事实确是如此:他使我们联结了宇宙。
巴赫的音乐,可以像衣服,每天穿在身上。今天我穿上《英国组曲》或者《法国组曲》,心情可以好得像花。明儿换一套《勃兰登堡协奏曲》,出席一场饭局。晚上再披一件《哥德堡变奏曲》,睡不睡得着又有什么关系。无论什么场合《十二平均律》随手套上。如果穿上《无伴奏大提琴组曲》或是《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帕蒂塔组曲》,都将是最感性的自己。
早上,我去跑步,在马路上看到挂着“热烈欢迎上海援鄂医疗队凯旋”的大巴。心里涌着酸楚,那些与亲人分别的日子,医护人员肯定非常思念和孤单;那些冒着病毒极大风险的日子,医护人员肯定需要十二分的勇气和力量。
送别“抗疫战士”的那一天,武汉市民自发在阳台上,大喊:“再见了,谢谢白衣天使,祝你们一路平安!”
而有些医务工作者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了抗疫的纪念碑上。
音乐忽然响起巴赫的《马太受难曲》。我们在前进的路上,总有人重如泰山。
首次演出马太受难曲,是在1729年的耶稣受难日的星期五。现存的唯一一份对此的评价,来自一位不知名的贵族夫人,她曾经说过:“上帝保佑!这不就是一场喜歌剧吗!”
所谓的“喜”,在当时理解为“戏剧”的意思。那位夫人听了受难曲,想到了歌剧,是可以理解的。巴赫的音乐是一种内在的和自发的戏剧形式,它不需要刻意去描写高度激情或是强烈情绪。巴赫的音乐,在听者的眼睛里,看到的是一部带着冲突与和解的戏剧;在听者的灵魂里,感受到的是一种宏浩的经历。那位夫人抓住了实质:她感受到不舒服,因为音乐震撼了她。
30岁时的巴赫在魏玛,自信的巴赫
前几天,有个朋友失恋了。放弃或许比坚持更难。人的一生,总是在成长,经历一些人,经历一些事。是好还是坏,也许直到要写墓志铭的时候才能知晓。我安慰不了她,给她放了马友友的《无伴奏大提琴组曲》。
疫情中困在家里的马友友用“萨拉班德”为一线医护人员纾困
大提琴,被誉为最接近人声的乐器。它或许可以代替我的语言,去抚慰她受伤的心。有时候,想说些什么呢?说什么都不如音乐来得管用。
1720年的鳏夫巴赫,悲伤的巴赫
同样抚慰人心的,巴赫还有一套《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与帕蒂塔组曲》。尤其在《b小调帕蒂塔》(BWV 1002)中,他显示了高超的作曲技巧,把同样的乐段再次插入到“复奏”中去,而且如此精确,达到了两者可以同时演奏的程度。连大师梅纽因都曾指出,这六首乐曲的六个调式,是最适合小提琴演奏的曲子,但也是没有符号或只有一个符号的最难的曲子。
这种复调的音乐就像人的内心复杂情感,纠结多过平静,欲望多过满足。
我曾经看过朗朗的一个MV,把《十二平均律曲集》中的第一首C大调前奏曲用影像描绘出来。无限变化的音符,让听者从人之生看到人之暮,从心之悲体会到心之喜。
巴赫在克腾的五年“是他一生中最开心最平静的时期”,他完成了大部分的《十二平均律曲集》。与其说,这部平均律集是教科书式的著作,不如说是巴赫用建筑的手法将音乐谱写成了一座动态的城堡。这座城堡,无论在任何时代,都不会过时。
还有一座城堡,不得不提。那就是《哥德堡变奏曲》。事实上,我们也可以称它为:《凯瑟琳伯爵变奏曲》。因为巴赫是为他而写的,凯瑟琳为此付给他丰厚的报酬:一只银杯和里面装满的100块路易金币。虽然这套变奏曲为了治疗凯瑟琳伯爵的失眠,但30种变奏已经不再镇静,几乎每一首变奏曲都是激动人心的。能不能助眠又有什么关系,有修养的行家凯瑟琳自然心甘情愿坠入这无比的欢欣之中。
1746年的巴赫,有明显眼疾的巴赫
如果说巴赫的音乐是最时兴的,我想没有人会辩驳。我们甚至可以在后来的贝多芬、莫扎特、门德尔松、舒伯特……部分音乐中读到那些熟悉的痕迹。
正如贝多芬所说,巴赫的名字在德语中虽然是“小溪”,实际他就像“大海”。
他的另一部《赋格的艺术》,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,是不可仿制的。巴赫证明了,一个主题也完全可以反过来或者倒过来,或者向前向后同时加以处理。
对于巴赫来说,上帝不仅存在于彼岸,而且也存在于我们的世界当中,不论他的命运遭受了多少打击,上帝仍然活在他的心中。
在1749-1750年间,巴赫除了加工《赋格的艺术》之外,还再次写下了各种众赞歌18首。在这期间,病痛一直缠绕着他。糖尿病在当时既无法确诊也无法治疗,并且引起的眼病对他简直就是灾难。他最后的众赞歌《我来到你的宝座前》,是他口述,他的女婿约翰·克里斯托夫·阿尔特尼科用笔写下的。
巴赫的墓碑上,
或许可以写上提摩太书第四章的词句:
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,
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,
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
莱比锡时期的巴赫,苦闷的巴赫
叔本华曾在他的“天才论”一文中说:“普通有才华的人,总是来得很是时候:来自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和需要;因而他们也只能有能力适合那个时代……对下一代人来说,他们的作品则不再可读,必然被其他所取代。但天才却不同,他们来到他们的时代,犹如一颗彗星进入天体轨道,但其独特的轨迹,却与井然有序和一目了然的天体运行迥然有别。”
感谢那个1685年3月21日出生的,叫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的人,是他让我知道了,信仰是什么。